一行人在營地外圍轉了一圈,最後來到一處壕溝邊,對面同樣是清軍營地隱約的燈海,連著天上的繁星,似乎分不清哪個是天,哪個是地。
隆冬的寒夜冰冷徹骨,這壕溝邊依著張誠的吩咐,把那些清兵的殘軀斷肢都堆砌在溝邊,再澆以冷水,如今確是凍得堅實。
燈火閃耀中,咋隱咋現,其狀猶似地獄一般,恐怖至極。
張誠身上披著盔甲,直有冷到骨子裡去的感覺,有時一股寒風吹來,他不由自主全身哆嗦,更不時聽到周邊各人牙齒上下相碰的聲音。
大明的北方,真冷,好在張誠在穿越前原本就是各北方人,而且這副身體也足夠壯健,饒是如此,他還是覺得這時的隆冬確為酷寒無比。
盧象升披著大氅,只是望著對面清營的燈海一動不動,良久,他忽然問道:「忠忱,此番入衛京畿,你可曾後悔過嚒?」
他曾親為張誠取了表字,且自馬坊之戰後,他一直對張誠極為讚賞,在他心中已隱隱想要把張誠培養成一代將帥,此子不止出身將門,更是童生,且入衛後軍功卓著,將來或不可限量。
聽盧象升如此問來,張誠不由心中怔了一怔,隨後微笑著道:「張誠自入得軍伍,便將死生拋之腦後,能追隨督臣殺奴衛國,實乃張誠平生所願,便是死,也死得其所!」
盧象升輕輕嘆了口氣,說道:「忠忱,你才識過人,又有忠君報國之心,陣前身先士卒,敢於奮勇在先,確屬難得,更兼聖上讚賞有加,前景一片光明,
如今跟隨在本督麾下,卻困在此地,隨時有覆亡之憂慮,前途莫測,你年齒尚淺,前途遠大,若是殞身於此,豈不可惜了!」
張誠聞言卻朗聲笑道:「督臣對末將有知遇之恩,援引之情,末將雖為一介武人,也曉得滴水之恩,當湧泉相報的道理,
更何況我輩軍人,自當胸懷以死報國之念,如今即陷韃虜重圍之中,正是我等報國之時,就殺他個痛快也好!」
盧象升站在原處,嘴裡喃喃說了句什麼,又嘆道:「你雖自稱武夫,卻比那大多文人更知忠義的道理;
如今朝堂之上袞袞諸公,雖飽讀聖賢之書,卻又幾人能如你這般見識。」
隨後他又繼續說道:「待此番奴賊退卻後,本督定要再向皇上懇請回家丁憂,自家嚴去世,我一直被皇上奪情留用,為人子女不能伴在身旁守孝,實為大不孝之罪。」
張誠溫言安慰道:「自古皆是忠孝難兩全,何況方今虜賊入寇的關鍵時刻,督臣切不可太自責了。」
盧象升聞言默默點頭,隨後裹緊身上的大氅,又道:「北地還是太過苦寒,雖數年在此,仍是不能適應,真懷念家鄉的景致啊。」
他轉頭對著張誠笑了笑,繼續說道:「若是日後本督回到南直,那時忠忱你到宜興來,本督定要倒屣相迎。」
張誠笑著打趣道:「如此,那就說定了,有機會末將一定上門蹭飯去。」
他們二人周邊跟隨的眾人都是笑了起來,盧象升也忍俊不禁地搖了搖頭。
當夜,張誠在軍帳中睡到三更時分,便被一陣隱隱傳來的觱篥聲吵醒,那是遠處清軍營地中傳來的,就像是四面楚歌一樣,或許是清兵用來瓦解宣大軍的鬥志的。
觱篥之聲顯得幽然而神秘,若隱若現迴蕩在靜寂的夜空之中。
張誠躺著聽了一會,乾脆坐起身來,他此時心潮澎湃,明日的戰事定必艱難無比,自己入衛以來的苦心孤詣,倒底能否改變賈莊之戰的命運?
往事一幕幕出現在他的眼前,自從來到這個世界,到如今才短短半年時光,卻叫他目睹了這時的人間悲劇,朝堂上權力黨爭不斷,已然超越人性的極限。
各地方官員貪生怕死,卻極盡徇私舞弊之能事,禍害百姓技法高超,遇到韃虜非逃即降,鮮有敢於拼死抵抗,為國盡忠者。
可他一路走到如今,已經是不能再回頭了,唯有一路下去,至於前路是光明,亦或黑暗
任他去吧,至少要站著活下去,只要手裡還有刀,就不能再容他人欺辱,就要砍殺出自己的明天!
心念及此,張誠輕嘆了一聲,說道:「來決一死戰吧,
『加入書籤,方便閱讀』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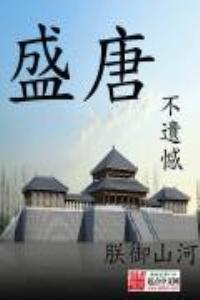 盛唐不遺憾 沒有屈辱和遺憾,只有勝利和輝煌。 鐵軌鋪向哪裡,大唐的利益就延伸到哪裡。 火炮戰車所向無敵,一帶一路再創輝煌。
各位書友要是覺得《盛唐不遺憾》還不錯的話請不要忘記向您QQ群和微博
盛唐不遺憾 沒有屈辱和遺憾,只有勝利和輝煌。 鐵軌鋪向哪裡,大唐的利益就延伸到哪裡。 火炮戰車所向無敵,一帶一路再創輝煌。
各位書友要是覺得《盛唐不遺憾》還不錯的話請不要忘記向您QQ群和微博 穿越1630之崛起南美 遼闊的潘帕斯草原、富饒的巴西、群雄角力的加勒比海…… 21世紀500人意外穿越南美,一切從生存開始。
各位書友要是覺得《穿越1630之崛起南美》還不錯的話請不要忘記向您QQ群和微博
穿越1630之崛起南美 遼闊的潘帕斯草原、富饒的巴西、群雄角力的加勒比海…… 21世紀500人意外穿越南美,一切從生存開始。
各位書友要是覺得《穿越1630之崛起南美》還不錯的話請不要忘記向您QQ群和微博 戰隋 大隋王朝為何驟然敗亡?隋煬帝是不是昏君?山東義軍為何蜂擁而起?張須陀為何不能力挽狂瀾?李密崛起中原,在鼎盛之期,為何突然隕落?群雄爭霸,最後勝出者,為何是李唐?一切秘密,盡在《戰隋》。
戰隋 大隋王朝為何驟然敗亡?隋煬帝是不是昏君?山東義軍為何蜂擁而起?張須陀為何不能力挽狂瀾?李密崛起中原,在鼎盛之期,為何突然隕落?群雄爭霸,最後勝出者,為何是李唐?一切秘密,盡在《戰隋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