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禎皇帝坐著御輦來到文華殿院中,遠遠看見陳新甲跪在甬路旁接駕。
御輦直到文華前殿的台階前才停下來,崇禎皇帝下了御輦,直接進了東暖閣,他在御座上頹然坐下,仿佛感到自己的心情和身體都十分沉重一般,顯得精神略有些萎靡不振的樣子。
陳新甲輕輕跟在後面進入暖閣內,他在崇禎皇帝面前跪下行過了常朝禮後,便靜靜地站立一旁等候著皇上的問話。
崇禎皇帝先是使了個眼色,閣內伺候的太監、宮娥們立即悄無聲息地退了出去。
整個東暖閣內只剩下崇禎皇帝與陳新甲群臣二人,登時變得沉靜無比,氣氛又沉默了片刻,崇禎皇帝才十分憂鬱地小聲說道:「朕今晚將卿叫宮裡來,是想專議關外與中原兩方之事。
錦州圍解,關外稍安,然亦非無慮,奴賊雖受挫於錦城之下,其元氣亦未見大傷,更有朝鮮可供其壓榨,想來不須多久,便可有所恢復。
我遼東防務亦要有所加強,切莫予奴賊以可乘之機!」
陳新甲小心回奏:「奴賊雖非大挫,然困錦兩年余,空耗錢糧,更損兵折將,此乃我朝十數年未有之大勝仗,卻也只微挫奴賊,未能傷其筋骨。
假以時日,但只奴賊稍作喘息,仍恐其又會趁我用兵於豫省剿賊之機,入犯京畿內地,行逞兵劫掠擄奪之事。
介時,我大軍皆與流賊對峙河南,又到何處招兵勤王,護衛京畿內地。若真如此,實無應對之策,恐唯有祈盼奴賊劫掠過後,會如往常一般,自行退卻啦。」
他自然知曉崇禎皇帝心中所想——既願與奴賊議和,又不肯自己首先提起!
「皇上,此斷不可不防,亦不可防而無備」
此刻,見崇禎皇帝對適才所言,並未有所表示,便大著膽子繼續說道:「皇上,微臣身為本兵,不能代陛下分憂,實在罪不容恕。
每日夜茶飯不思,苦苦冥想,為今之計,怕只有一策,方能使我可專心剿賊,安定中原腹地啦」
陳新甲說的每一句話,都十分小心翼翼,他不止是緩緩而言,更時刻關注著崇禎皇帝的表情,甚至連他肢體上的細微變化都不敢放過。
只見聽了陳新甲這番話後,崇禎皇帝的神情似乎有所提振,他輕聲問著:「卿有何良策,速速說來!」
「微臣以為,若要保遼東無事,使京畿無警,可專心圍剿流賊,安定中原腹地。恐惟有與奴和議之一策了。」
崇禎皇帝忽又問了句:「除此就別無他法了嗎?」
陳新甲微微垂下了頭,默然無語,不敢作答。
良久,崇禎皇帝才輕輕嘆了口氣,道:「如今內外交困,財力枯竭,又兵乏將疲,士無鬥志,惟有苦心經營,先剿流賊,再御東虜。
為今之計,為了中興大明,只好暫對東虜議撫使遼東局勢稍顯緩和,才好全力對內用兵,剿除流賊,安定中原腹心之地。」
崇禎皇帝也是在今天晚間,才剛剛接到了河南來的飛奏:河南巡撫高名衡奏報,陝西、三邊總督汪喬年在襄城兵敗,李自成於二月十七日攻破襄城,將汪喬年捉到,殺在城外。
幾天以前,崇禎皇帝才剛剛知道平賊將軍左良玉與李自成正在郾城相持,而汪喬年此時也正要往襄城進兵,好會同左良玉部官軍一起夾擊闖賊。
沒有料到真的是萬萬沒有料到!
他怎麼會失敗得這麼快呢?
竟然就這麼死了!
崇禎皇帝怎麼也想不明白:左良玉的官軍到哪裡去了?
汪喬年的數萬人馬,怎麼一到襄城,就被闖賊擊潰了呢?甚至連汪喬年自己都殞命襄城?
倘若是以前,他得到這份奏報必定會感到十分的震驚,且在震驚過後,很可能還會跑到奉先殿去痛哭一陣。
然而,自從前督師、閣老楊嗣昌死於沙市軍前後,他也已經逐漸習慣了督臣戰亡之事,前次陝督傅宗龍戰亡於項城,他便與今次一般,只覺得灰心,愁悶,憂慮,而不再前去奉先殿哭殿了。
或許,傅宗龍和汪喬年這兩個三邊總督,在他心目中的分量還是不夠重,壓根兒就不能與督師楊嗣昌相提並論。
『加入書籤,方便閱讀』
 明天下 明末的歷史紛亂混雜,堪稱是一段由一些有着強大個人魅力的人書寫成的歷史。 不論是李自成,還是張獻忠這些叛逆者,還是崇禎,袁崇煥,這些當權者,亦或是吳三桂,耿精忠這些背叛者,每個人身上都有很多的
明天下 明末的歷史紛亂混雜,堪稱是一段由一些有着強大個人魅力的人書寫成的歷史。 不論是李自成,還是張獻忠這些叛逆者,還是崇禎,袁崇煥,這些當權者,亦或是吳三桂,耿精忠這些背叛者,每個人身上都有很多的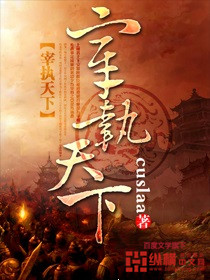 宰執天下 宰者宰相,執者執政。 上輔君王,下安黎庶,群臣避道,禮絕百僚,是為宰相。 佐政事,定國策,副署詔令,為宰相之亞,是為執政。 因為一場空難,賀方一邁千年,回到了傳說中『積貧積弱
宰執天下 宰者宰相,執者執政。 上輔君王,下安黎庶,群臣避道,禮絕百僚,是為宰相。 佐政事,定國策,副署詔令,為宰相之亞,是為執政。 因為一場空難,賀方一邁千年,回到了傳說中『積貧積弱 漢兒不為奴 雲從龍,風從虎,功名利祿塵與土
望神州,百姓苦,千里沃土皆荒蕪
看天下,盡胡虜,天道殘缺匹夫補
好男兒,別父母,只為蒼生不為主
手持鋼刀九十九,殺盡胡兒
漢兒不為奴 雲從龍,風從虎,功名利祿塵與土
望神州,百姓苦,千里沃土皆荒蕪
看天下,盡胡虜,天道殘缺匹夫補
好男兒,別父母,只為蒼生不為主
手持鋼刀九十九,殺盡胡兒